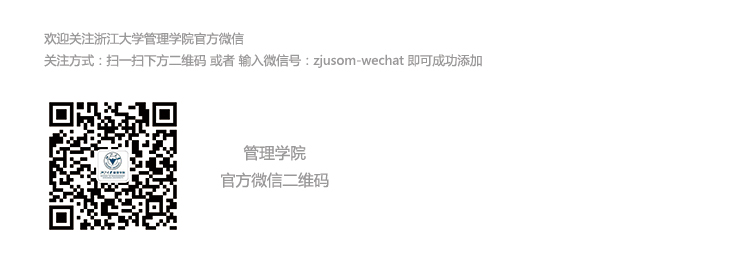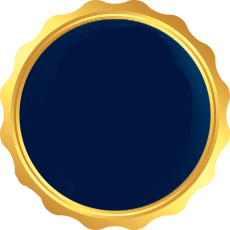浙大管院汪蕾团队发现 人类抗拒不公平是有条件的
近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汪蕾(通讯作者)与浙大管院2017级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李欧、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徐富明共同在《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不公平”现象的研究——《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Does Not Always Exist: The Role of Determining Allocations Modulates Preferences for Advantageous Inequity》。
该研究发现,人类抗拒“我比你多”式不公平是有条件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它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结果一经发表,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一般而言,“公平”的本质可以用行为经济学中的不公平规避模型 (inequity aversion model) 来描述。根据该模型,人们天生就会追求公平,甚至为了公平愿意放弃一定的个人利益。
而“不公平”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干了同样的活,但我的收入比你少,即“我比你少”式不公平;而另一种则是干了同样的活,但我的收入比你多,即“我比你多”式不公平。
过去的研究普遍认为,当“我比你多”式不公平出现时,追求公平是人类的天性,人类愿意主动放弃既得的好处以维护一个公平的结果。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情心已相当成熟,也可能是人类所发展出的愧疚等高级情绪使然,因此,人类才会在处于优势地位时怜悯、同情弱者。
然而,汪蕾团队的研究却发现,个体对“我比你多”式不公平的厌恶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普遍。至少当人们在分配中没有“话语权”时,他们并不会表现出对这种不公平的厌恶。
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误解”
目前在研究“我比你多”式不公平时,通常是让被试主动决定如何与另一名参与者分配一笔钱。比如10元钱,被试既可选择全部拿走,也可选择分配任意份额的钱给另一方。
而在研究“我比你少”式不公平时,则是向被试呈现一个分配方案,再由被试评估他对这个方案是否满意或是否接受。
很明显,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在“我比你多”的范式中,被试可以主动决定分配方案,也就是说,他在分配中拥有主动性;而在“我比你少”的范式中,被试则没有办法决定分配过程,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个预先决定的方案。
可见,现有的研究在讨论“我比你多”和“我比你少”时,都是直接将它们进行比较,并认为人们都会厌恶这两种形式的不公平。
然而,研究方法上的不一致,使得这种“直接比较”看起来并不严谨。虽然在主动决定分配方案的范式中,研究者发现了人们会非常厌恶“我比你多”这种情况。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们不能决定分配方案,就像“我比你少”范式中那样,那人们是否还会厌恶“我比你多”这种不公平呢?
厌恶“我比你多”式不公平,是有条件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厌恶“我比你多”式不公平,是有条件的,即被试在分配中是否拥有主动性(能否决定分配方案)。
实验总共招募了141名被试,在任务中,他们需要和另一位匿名参与者共同完成一个分配任务。在每一轮任务中,被试都要考虑如何与另一个人分配10元钱。
其中一半的被试在分配中能够决定分配,即拥有主动性。比如在(8,2)(左边数字为分给自己的钱,右边为分给他人的钱)和(5,5)之间选择一个方案作为最后的分配结果。而另一半被试,则无法决定分配,他们只能被动接受一个预先由计算机决定的分配,并评估自己对它是否满意。
依据显示偏好理论,决策者始终会选择令他们效用最大(即满意度最高)的选项。因此,决策者实际做出的选择,就是他们最为满意的选项。这样在主动条件下的二选一,便与被动条件下的满意评估统一在了一个量纲下。
在开始每一轮任务前,被试和匿名参与者还要共同完成一道智力题。只有在双方都回答正确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进入分配阶段,也只有在双方付出同等努力后得到有差别的收入,才符合公平概念的一般含义。因为通过智力可以控制双方的成本因素,使得他们的公平感受更为真实。
结果显示,在主动条件下(图1 中红色),被试无论是对“我比你多”,还是对“我比你少”的偏好,都要远远低于对公平分配的偏好,而且对它们的偏好程度都低于20%;然而在被动条件下(图1 中蓝色),被试对“我比你多”和“我比你少”的偏好却出现了异化。此时,他们只厌恶“我比你少”,但对“我比你多”的偏好却高达80%以上,而且和对公平的偏好没有差异。
图1:左边为主动条件下的情况,右边为被动条件下的情况。横轴是不同的分配类型,括号内左边数字是分给被试的钱,右边的数字是分给同伴的钱。纵轴是对不同方案的偏好概率。
这个实验结果非常明显地证明,当人们在分配中能主动决定分配时,他们迈向了公平;而一旦只能被动接受一个分配时,他们便抛弃了公平。
不同条件下遭遇不公平,情绪反应不同
在随后的实验中,我们想弄明白:在主动和被动条件之间,被试仅仅是在行为上存在差异,还是在(不公平)情绪上也存在差异呢?
由于问卷或自我报告等方法并不能有效测量被试的真实情绪反应,因此我们使用到了多导生理记录仪来测量被试的皮肤电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 SCR)。
SCR是一种由情绪引起的生理-心理反应,它能即时表征个体的情绪活动。由于情绪是不公平体验背后的重要“推手”——不公平本质上就是一种消极情绪,因此现有研究者经常用SCR作为个体所体验到的不公平程度指标。体验到的不公平程度越高,个体的SCR水平也越高。
在记录并分析被试的SCR之后,我们发现不公平结果(比如说被试得8元,同伴得2元)在主动条件下所引起的SCR要远高于公平结果。这就说明,在主动条件下,“我比你高”让被试体验到强烈的不公平感受。
然而,在被动条件下,同等程度的不公平结果所引起的SCR却与公平结果一样低,“我比你高”引起的情绪波动与公平结果无差异,换句话说,此时被试并没有体验到强烈的不公平感受。
该结果从生理层面重复了我们前面的结果,只有在人们参与并能决定分配的情况下,他们才能体验到“我比你多”所带来的真真切切的不公平感受,然而在人们不能决定分配时,“我比你多”并不会产生不公平感受。
企业管理者要为员工创造“主动条件”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管理实践中涉及到公平问题(比如工作分配、绩效管理)时,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到员工所处的位置。因为处在分配不同环节上的员工,对同样的方案可能存在不同的公平感受。
企业管理者该如何去兼顾公平?或者说,企业应当如何尽量避免员工的不公平感受呢?
由于个体在主动条件下更能遵守公平,因此,企业在分配或者绩效制定中,可以适当引导员工积极参与,通过确立他们的主动地位,来激发他们的公平行为,从而更和谐地统筹分配工作。
参考资料
Bolton, G. E., and Ockenfels, A. (2000). ERC: a theory of 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 Am. Econ. Rev. 90, 166–193.
Fehr, E., and Schmidt, K. M.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 J. Econ. 114, 817–868.
Fehr, E., and Schmidt, K. M. (2006). “The economics of fairness, reciprocity and altruism: experimental evidence and new theories,” i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Giving, Altruism and Reciprocity, eds S.-C. Kolm and J. M. Ythier (Amsterdam: Elsevier), 615–691.
Gollwitzer, M., & Prooijen, J. W. V. (2016). Psychology of Justice.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Springer New York.
Sanfey, A. G., Rilling, J. K., Aronson, J. A., Nystrom, L. E., and Cohen, J. D. (2003).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Game. Science 300, 1755–1758.
Samuelson, P. A. (1938). A note on the pure theory of consumer’s behaviour. Econimica 5, 61–71.
Van’t Wout, M., Kahn, R. S., Sanfey, A. G., and Aleman, A. (2006). Affective state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Exp. Brain Res. 169, 564–568.